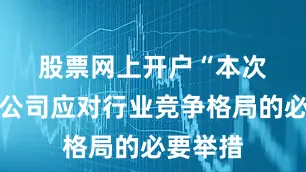孔子生逢春秋末期,其时礼崩乐坏,虽尚未像战国乱世那么“不讲武德”,但诸侯国不服周王室已昭然若揭,孔子不由生出“吾道不行”的慨叹。那么,孔子向往的理想社会是什么样子呢?“周监于二代,郁郁乎文哉!吾从周。”孔子向往的是周公制礼作乐的西周社会。
西周礼乐文明从殷商时期的敬鬼神涅槃而生,张扬人的主体地位和理性价值,是中国人不断回望的文明基石。
现代人可以通过什么方式了解两三千年前的西周社会呢?通过《诗经》。
《诗经百句(口袋本)》实拍书影
《诗经》是跨越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500年间的诗歌总集,从中可以看到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丰富的思想情感,是我们了解孔子向往的理想社会的一面镜子。
“男大当婚,女大当嫁”是中国人的朴素信念,体现了中国人对婚姻和家庭的重视,影响了中国数千年。《周南·关雎》书写了男子对心上人的思慕,“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;《秦风·蒹葭》描绘了对爱情的上下求索,“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”;《邶风·静女》让我们看到了恋爱中约会时的“翘首以盼”,“爱而不见,搔首踟蹰”;《郑风·子矜》活灵活现地传达了恋爱男女的小别扭,“纵我不往,子宁不嗣音”;《卫风·木瓜》定格了情人间相互赠送礼物的表情达意时刻,“投我以木瓜,报之以琼琚。匪报也,永以为好也”;《周南·桃夭》像在“直播”一场春天的婚礼,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,宜其室家”;《邶风·击鼓》为后世提供了最为浪漫的爱情誓言,“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”;《郑风·女曰鸡鸣》描画出婚姻生活的和谐美满,“琴瑟在御,莫不静好”;《周南·螽斯》直抒多子多福的婚姻祝福,“螽斯羽,诜诜兮。宜尔子孙,振振兮”。
展开剩余60%[清] 弘历《御笔诗经全图书画合璧图册》(局部)
西周取代强大的殷商而立,《大雅·文王》歌颂了“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”的革新精神;西周以小邦国统治大中原,以联姻为手段,在宴饮中歌颂异姓诸侯的兄弟情,如《小雅·鹿鸣》之“我有嘉宾,鼓瑟吹笙”,《小雅·常棣》之“凡今之人,莫如兄弟”。
《诗经》中的战争描写并不意在宣扬战争,而是弥漫反战、厌战情绪,行动上又是同仇敌忾、保家卫国的:既有《小雅·采薇》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”的厌战思归,又有《秦风·无衣》“岂曰无衣?与子同袍。王于兴师,修我戈矛,与子同仇”的以战止战。《诗经》中的农事描写既有繁重的生计艰难,又有劳动的愉快体验。《豳风·七月》记录了一年农事的有条不紊和劳作后的休闲,《周南·苤苢》记录了女子成群结队漫山遍野采车前草的欢快劳作场景。《诗经》同样写了底层小人物的勤苦无告:《小雅·何草不黄》“何草不黄?何日不行?何人不将?经营四方”言说生活的艰辛和悲苦,《召南·小星》“嘒彼小星,三五在东。肃肃宵征,夙夜在公”,倾诉披星戴月奔忙公务的无助心情。千古一心,今天的我们同样热爱和平、向往张弛有度的生活、默默坚守平凡的岗位。
[清] 弘历《御笔诗经全图书画合璧图册》(局部)
在温情脉脉的礼乐之外,《诗经》并不逃避社会矛盾。孔子曰:“《诗》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。”“怨”的功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。《魏风·硕鼠》痛斥贪婪的剥削者对劳动者的掠夺,“硕鼠硕鼠,无食我黍。三岁贯女,莫我肯顾”。《魏风·伐檀》刻画了不劳而获者的丑恶嘴脸,“不稼不穑,胡取禾三百廛兮?”
《诗经》产生于“人文化成”时期,建构了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品格——重伦理、敬自然、尚人文。《诗经》中的大部分篇章都产生于西周时期,透过孔子所推崇的理想社会,我们看到先民热气腾腾的生活和真诚不欺的情感。每代人所面临的时代难题和社会困境都不一样, 《诗经》诞生时的社会也远非理想状态,但“花似人心向好处牵”,我们可以感受农耕时代的朴素向上,可以学习生命的“向好而生”。
刘冬颖教授的《诗经百句(口袋本)》甄选“百句”《诗经》文本,关涉婚恋、农事、宴饮、祭祀、战争等诗篇,加以明白如话的解读,为我们呈现了先民活泼泼的生活样态和心灵生态。 《诗经》重章叠句,从文本还原到它所产生的时代,可称为“歌词”,是入乐的,表达情绪和情感,为生活“减压”。刘教授不仅以笔著书,还以古调吟唱《诗经》,重现了它的原生态之美。
发布于:上海市富华优配-股票配资那个正规-苏州股票配资公司-配资炒股平台首选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配资中介天秤座因其追求和谐、善于平衡的特点
- 下一篇:没有了